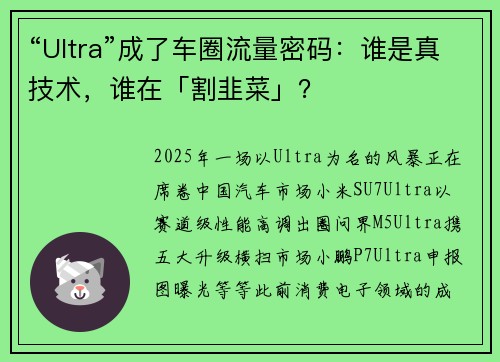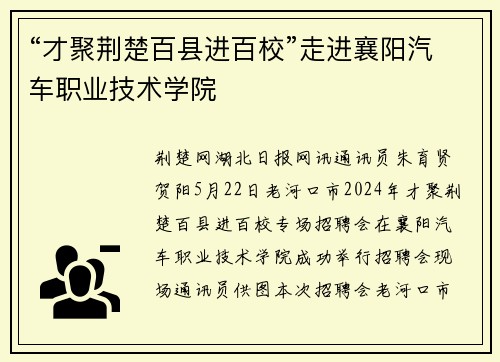“共和国长子”的破产重组,沈阳机床厂是怎么把自己搞垮的?
机床在制造业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,被称作“工业母鸡”,是制造机器的机器。在制造业,若想涉足汽车、坦克、高铁、飞机乃至航母等领域的制造,机床便是首要攻克的“科技关卡”。

自工业革命后的数百年间,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实现指数型发展,根源就在于机器能够自我制造,而机床无疑是这一进程中当之无愧的“工业之母”,处于整个制造业最上游、最基础的环节。车、铣、镗、磨、钻、刨等加工工艺,承载着人类开拓未知领域的梦想,而这一切都始于机床。

冷战时期,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“东芝事件”。1983年,日本东芝公司出于商业利益考量,将4台数控机床出售给苏联。
苏联借助这些机床制造潜艇部件,竟在一夜之间大幅提升了核潜艇的噪音控制能力。几台数控机床,就此影响了大国间的战略博弈,动摇了核平衡的微妙态势,其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那么,中国的机床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呢?用“大而不强”来概括最为恰当。
从数据来看,2019年全球机床行业产值达842亿美元,中国以194亿美元的产值占比23%,位居世界第一;全球机床消费额为821亿美元,中国消费额高达223亿,同样位列世界首位。
单纯从数量和消费规模上看,传统机床强国德国和日本都难以望其项背。然而,高端制造业,尤其是机床行业,有着独特的评判标准。
中国虽在规模上领先,但在高端领域,几乎处于失守状态,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;中端领域面临着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机床企业的激烈竞争,鏖战正酣;低端领域则陷入严重的内卷困境,呈现出“高端失守,中端争夺,低端内战”的复杂局面。
提及中国机床,就不得不说中国第一大机床厂——沈阳机床。它曾是国企改革的明星典范,一度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床企业,在最辉煌的时期,年销售额高达180亿元。
但令人惋惜的是,2019年8月,仅仅一笔400万的债务违约,就将其彻底压垮,不得不进入重组程序。从中国制造业的骄傲之巅跌落至破产重组的谷底,沈阳机床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。
建国初期,在苏联的援助下,我国大力推进“一五计划”,全面开启工业化建设的宏伟篇章。国家重点扶持了18个机床企业,即赫赫有名的“十八罗汉”。
彼时,沈阳堪称中国工业皇冠上的璀璨明珠,辽宁更被誉为“共和国工业长子”。在“十八罗汉”中,辽宁独占四席,沈阳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机床厂以及大连机床厂风光无限。
沈阳的铁西区,被称作“中国的鲁尔”,作为“共和国长子的钢铁心脏”,沈阳三大机床厂均坐落于此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它们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制造业输送着强大动力。
然而,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转型,东北工业面临着巨大的阵痛。
铁西区众多曾经举足轻重的企业逐渐走向衰落,三大机床厂的固定资产净值一度降至巅峰时期的四成。历经几十年的高强度生产,设备严重老化,半数以上的设备使用年限超过20年。
1993年,在沈阳市政府的主导下,三大机床厂与其他几家企业合并,组建了沈阳机床(简称沈机)。但沈机刚一成立,便陷入进口机床和新兴小机床厂的重重围剿之中。
此后的10年,沈机一路下滑,亏损不断,员工数量锐减六成。这也是当时中国机床行业的普遍困境:利润微薄,经营举步维艰。
2002年,年仅38岁的关锡友出任集团总经理,成为沈机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。
2003年10月,国家出台政策加大对东北的支持力度,沈机迎来了发展的风口。在关锡友的领导下,沈机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剥离所有非主业,随后展开一系列收购扩张行动。
2004年,沈机率先收购德国希斯公司,紧接着将国内的云南机床、昆明机床纳入麾下。从2002年到2011年,沈机销售额从13.6亿元飙升至180亿,世界排名也从第36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。
关锡友曾总结这一时期成功的三点因素:一是中国经济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,机床市场需求激增,沈机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期;二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有力支持;三是沈机自身的传承与不懈努力。
但是,沈机虽然规模迅速扩张,却并未真正做强。并购虽然扩大了沈机的体量,但其在国际机床行业的层级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。
沈阳机床的技术水平仍停留在低端领域,尽管能够生产中端、高端机床的外壳,但其核心数控系统却依赖进口,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发那科牢牢掌握着数控系统的核心专利。中国企业每销售一台机床,都需向德日企业支付高昂费用,利润分配呈现“三七开”,德日企业占据大头。
这一问题并非沈机独有,而是整个中国机床行业面临的共同难题。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,中国机床企业深知,不向高端突围转型,必然会被淘汰;然而,尝试转型之路充满未知,需要付出巨大代价。
关锡友比业内许多人都更清楚这一道理。他决心带领中国机床实现突围,2007年,他找到老同学朱志浩,在上海成立研究中心,开始研发自主数控系统——I5。
关锡友对I5寄予了极高的期望,希望其能领先发那科、西门子至少5年。为了打赢这场研发攻坚战,他几乎倾尽全力,在5年时间里,仅纯研发投入就高达12亿人民币,总投入更是达到30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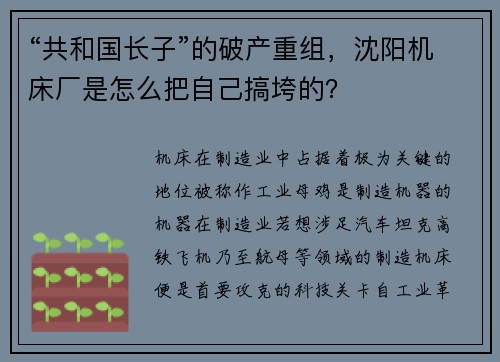
但问题在于,沈机本身资金并不充裕。尽管沈机是世界最大的机床企业之一,但其长期处于负债经营状态。以2011年为例,当年沈机销售额180亿,净利润却仅有1亿,负债率高达86%,财务状况极为脆弱。
为了筹集研发资金,关锡友采用了向商业银行借用短期贷款支撑长期研发投入的做法,甚至动用了资金杠杆,这使得沈机从此深陷债务泥潭,每年盈利仅够勉强支付利息。
2012年,I5数控机床终于研发成功,然而上市后却饱受争议。I5仅在低端的二轴、三轴数控机床上实现了大规模应用,且多数时候仅沈阳机床自身使用。对于中高端的多轴机床,沈机依然只能采购西门子、发那科的数控系统。
简而言之,I5未能契合行业对高端数控机床的需求,也未能为沈机带来预期的逆转。但关锡友依然坚定地相信,I5未来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甚至能够重新定义工业经济。
由于沈机规模虽大但现金流状况不佳,为了让I5数控系统能够持续发展,沈机另辟蹊径。当时共享经济概念盛行,沈机从中获得灵感,将共享经济与机床相结合,推出机床租赁业务。
主要模式有两种:一是直接出租机床;二是建设工业园区,即“5D制造谷”。其操作模式通常是与当地政府谈判拿地,建设配备I5机床和基础设施的工业园区,吸引客户入驻并收取租金。
2017年底,沈阳机床在全国签约了23个制造谷。然而,这一模式并未取得成功。数据显示,仅有3个制造谷勉强运转,且开工率极低,大量机床闲置。同时,租赁模式资金回笼缓慢,进一步加剧了沈阳机床原本紧张的现金流。
此外,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对沈机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201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,中国经济进入产业调整、转型升级阶段,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,对高端定制机床的需求日益增长,但行业供给能力却未能及时跟上,导致竞争加剧,整个机床行业开始走下坡路。作为国内最大的机床企业,沈机首当其冲受到冲击。
内因与外因相互交织,自2011年达到巅峰之后,沈阳机床的业绩再未亮眼过。2012年至2018年,沈阳机床的利润和现金流常常为负数,累计亏损高达50亿。
2017年,沈机已连续两年亏损,按照规定,若再亏损将面临退市风险。为保住上市公司地位,沈机采取了一系列问题企业常用的财务手段。
例如,部分债权人为降低债务风险,主动豁免沈机一些债务(会计学上称为债务豁免,应计入资本公积),沈机却将这些豁免债务计入营业外收入;沈机旗下的昆机也沦为财务造假工具,经证监会查明,2013年至2015年,昆机通过多种手段虚增收入4.8亿,年报中的存货数据也存在虚假记载;此外,沈机还将制造谷中出租的机床全部算作已出售,进行自卖自买的虚假交易。
除了财务造假和债务豁免,沈机的第三招是剥离资产,将部分业绩不佳的业务转给关联方,2017年就将非I5业务的资产与负债转出。尽管通过这些手段,沈阳机床在2018年财报中实现了1.18亿的盈利,暂时避免了退市,但这终究无法挽救其颓势。
2018年,沈机净利润为 - 7.8亿,2019年半年报显示亏损14亿,当年沈机被裁定重整。
谈及沈阳机床,人们的心情颇为复杂。它曾承载着中国机床高端突围的希望,但其失败又给行业带来沉重打击。不过,沈机的尝试也为行业留下了宝贵经验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
其一,高端制造业具有反经济常识、反直觉的特性,必须摒弃单纯的财务报表论。现行经济规律往往以增长和利润为首要目标,习惯通过财务报表来判断一个行业、企业或产品的前景。然而,高端制造业常常需要在未知领域深入探索,回报周期漫长,初期投入巨大且难以看到即时回报。
财务报表和资本市场更多反映的是短期投入,难以展现高端制造业更为长远的发展潜力。以华为为例,任正非曾透露,华为拥有15,000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(不包括应用研究人员),正是因为华为对高精尖人才的大力投入,才使其在关键时刻能够拿出可靠成果。
其二,工业统筹至关重要,需要从宏观层面加强规划。关锡友被一些人称为“国企赌王”,有一定道理。他领导下的沈机,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机床企业,但其决策却过于冒进。在推进数控机床研发时,缺乏循序渐进的规划,而是孤注一掷,甚至贷款加杠杆投入研发;研发成功后,又贸然涉足共享经济领域。
同时,沈机在国内外通过收购兼并迅速扩张规模,这种激进的扩张方式更像是金融游戏。如此做法或许能在资本市场讲出动听故事,却难以打造出真正的高精尖产品。高端制造业的技术攻关需要长期积累、充足时间以及大量试错,这就要求提前做好统筹规划和布局。
前苏联早在1946年就开始布局一批科学城,如车里雅宾斯克40、乌法105以及著名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。
这些城市按照全苏最高标准配备文化、娱乐、医疗、教育等设施,但人口可能仅有十几万甚至几万,其中三分之一是科学家,三分之一是家属和服务人员,三分之一是孩子。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专注于基础科学和高端产业研究。
这些投入短期内难以产生效益,却持续投入数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,一旦有所突破,便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劲动力。如今,这些科学城的成果依然照耀着俄罗斯科学界。
与之相比,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投入方面,力度和统筹性仍有提升空间。例如,中国天眼22年总投入仅6.69亿,而I5研发却耗费30亿且效果不佳。
华为凭借先进管理模式和超前研发思路,在本领域跻身世界一流,值得称赞。但中国不能仅有华为这样备受瞩目的明星企业,还需重视那些相对“隐形”却对国家至关重要的高端制造业企业。
因为多数高端制造业远离大众生活,关注度低,需要长期坚守。华为培养了1.5万名科学家,而中国每年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多达10万,然而多数人读博时补助微薄,毕业后还面临结构性失业,被迫转向来钱快的领域。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,却出现工业尖端人才过剩的现象,这值得中国制造业深刻反思。
此外,对于关乎国家战略的企业,不能过度追求好看的财务报表,更不应将其与高管KPI过度关联。如今会计学高度发达,企业很容易通过财务手段做出符合期望的数据。
沈阳机床、獐子岛等企业便是前车之鉴,通过财务操作打造出看似辉煌的数据,一旦泡沫破裂,企业倒闭,众多熟练工人失业,这无疑是对国家命脉行业的极不负责任。
文本素材来源@科工力量